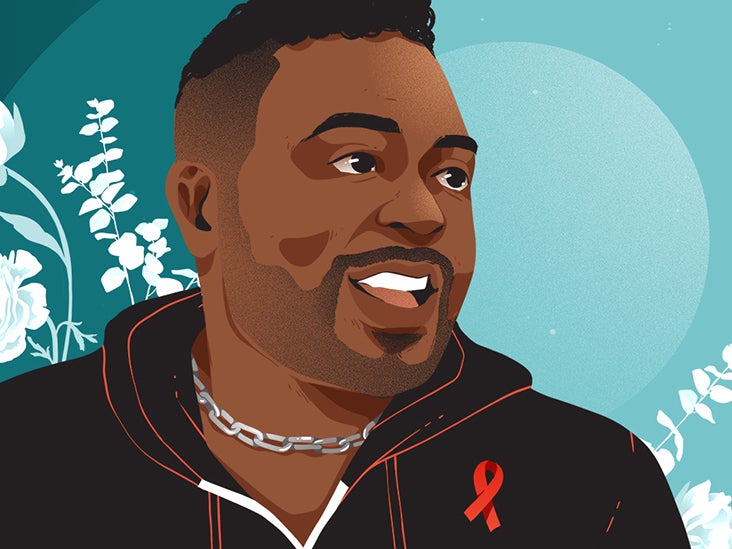我记得我的慢性疾病从内心开始发作。一阵脑雾,筋骨酸痛,像流感一样发冷,淋巴结和眼睑肿大,还有头晕。所有慢慢出现的症状一下子就消失了。
穿过房子就像在糖浆中跋涉一英里。社交互动变成了我无法再处理的词汇和社交线索的感官万花筒。我觉得自己像是被麻醉了一样。
我生活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这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导致身体所有部位和器官发炎;这是系统的形式红斑狼疮.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免疫系统变得混乱。它会错误地攻击人体自身的健康组织,包括肾脏、心脏和肺等器官。
许多患有狼疮的人都会经历器官的参与在他们患病的过程中这让我们这些还没有发现器官损伤的人陷入了等待的境地,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或何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每天都能感觉到狼疮——在我的肺里,在我的神经和肌肉骨骼系统里,在我的大脑里——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完成任何东西。有人悄悄说,它在血液检测中的存在足以证明红斑狼疮(SLE)的诊断,但还不足以说明它的位置或计划做什么。
所以,我的诊断仍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器官和系统受累不明。”直到现在,也许吧。
我的疾病诊断过程可以追溯到我被感染的大学时期莫诺,或爱泼斯坦-巴尔病毒.但是,大多数患有单性接吻症的年轻人只睡一两个星期就会把“接吻病”当作一种烦恼,而我却发现,在我本该痊愈的几个月后,自己越来越累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开始疲劳发作这可能持续几小时到几天,甚至几周。我把这些时间归因于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突然发作”,在卧床休息一两个星期后就会自然过去,就像轻度流感或感冒一样。我把他们的异常正常化了因为常规血液检查总是正常的。直到有一天我的身体“崩溃了”。
在她的书中看不见的王国,作家Meghan O 'Rourke将自己的发病比作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对破产的描述:“逐渐地,然后突然地。”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不过,尽管有持续不断的虚弱的疲劳,脑雾医疗专业人士向我保证,这是一种会传播的病毒,并建议服用抗焦虑药物作为治疗。
随着我的症状越来越多,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小。
22岁时,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搬到全国各地,回到我的家人身边,因为独自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在我的免费、国家资助的医疗保险下,我开始了我的巡回诊断,向任何愿意为我看病的过度劳累和不堪重负的医疗专业人员进行诊断。
我的初级保健医生诊断我患有抑郁症。一个心理学家叫我“高度神经质”。一位传染病医生再次声称自己感染了eb病毒。和一个风湿病学家看了一眼我的病历就告诉我慢性疲劳综合症/肌痛性脑脊髓炎(CFS/ME),我必须“学会与它共存”。他们甚至没有做常规血液检查来筛查自身免疫性疾病。
我厌倦了医生的预约和无效的药物,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体医学中——抗病毒补充剂、草药酊剂、绿色冰沙。从咖啡因到糖都能引发症状,我发现自己早餐、午餐和晚餐都吃羽衣甘蓝和藜麦。即使避免了大多数炎症性食物,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床上度过的。
在这一点上,我不仅筋疲力尽,而且很生气。对漠视我的医疗系统感到愤怒,对忽视我的症状感到愤怒,对以感恩日记和生生姜为中心的治疗建议感到愤怒,对医疗专业人员感到愤怒,他们在经过几个月无效的治疗后,举起双手告诉我,我的疾病“都是我的幻觉”。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几个朋友也经历过类似的、令人不屑的医疗经历(其中一个后来被诊断出患有另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强直性脊柱炎).在网上寻找慢性疲劳的答案时,我发现网上论坛上充斥着与我们相同的故事。
被告知症状都在我们的脑海中,这远非不正常。事实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在午睡的间隙,我和我的本科导师开始了一项研究,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健康传播。我们试图打破有关“看不见的、有争议的”疾病和“歇斯底里的”女性患者的有害医学言论。
我们的第一项研究重点是女性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家庭成员、朋友和社会那里收到的关于生殖和性健康的信息。讨论的结果什么消息我们是社会化与而不是我们真希望我们收到了.
当这项研究进行时,我专注于“治愈”——发现自己在与确诊的EBV感染作斗争时精力更充沛了。
SLE患者易患慢性和复发性感染以及EBV
我对我们的研究充满激情,并确信我正在变得“更好”,因为我每天的午睡时间从三个小时减少到一个半小时,我申请了一个人际关系和健康沟通的硕士课程,以研究患有隐形和未诊断慢性疾病的年轻人的信息。为了寻求宣泄、目的和合法性,我想证明这一切并非“都在我们的头脑中”。
但当我在那年秋天开始我的第一个学期时,我“正在好转”的残酷现实让我措手不及,症状的浪潮再次袭来。
我早上上课,下午打个盹,直到闹钟把我惊醒,然后拖着疼痛的身体去参加晚上的研讨会,一天比一天更像僵尸。
那时我已经看了9位医生,我不认为第10位医生会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克服了这些症状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
患有一种看不见的慢性疾病,反复被告知“这都是你的幻觉”,这让你开始对自己和自我意识失去信心。
病人不想回到医疗的旋转木马上——这是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过程——他们不再寻求医疗护理,害怕新的医生会重新揭开不被相信的伤疤,而他们将被留下来愈合现在更深的伤疤,再一次。
尽管如此,在绝望中,我还是去了大学的健康中心,告诉他们我的诊断是慢性疲劳和EBV。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会用“新鲜的眼光”来看待我的症状,而不是指望他们能发现任何新的东西。但令我惊讶的是,一位天使般的执业护士(NP)证实了我的症状,并说她会尽一切努力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两天后,这个NP打电话告诉我ANA测试呈阳性的消息。她知道这可能预示着自身免疫,她说:“我们不碰这个,我们建议你去看风湿病专家。”
健康中心的确认和新的检测结果证实了我一直以来所知道的:这些症状并不“都是我的想象”。所以我回到了医疗的旋转木马上。
正确的测试
ANA是“抗核抗体”的缩写。一个ANA血检检测血液中是否有自身抗体,这可能发生在感染和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有几种类型的ANA血液面板,这取决于你使用的实验室和你的医生正在筛查。
我在一项名为“反射性ANA”的测试中呈阳性,但在一般ANA面板中呈阴性。如果我早知道要做更彻底的检查,我可能就不会花5年时间得到狼疮诊断。
在等待了两个月的风湿病预约后,我被诊断为“未分化”结缔组织病“我的风湿病医生给我开了抗疟疾药羟氯喹这种药物通常用于治疗狼疮。
虽然怀疑是SLE,但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合格血液检查,无法满足美国风湿病学会的要求诊断标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认真地参加了每一次风湿病预约,注意每一个新的症状光敏性增加关节疼痛和皮疹——而且每一次都在消退。
在服药期间,我的精力正在恢复,脑雾正在消散,多年来的身体症状也变得可以忍受了。这似乎超过了药物的副作用,对我来说,这表现为某些心理健康症状的恶化,后来被诊断为强迫症.又是一次疾病之旅。
在我的研究生课程中,我开始写论文关于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年轻人在诊断过程中学习和接受的教训,采访了我这个年龄的人,他们也经历过长期、艰苦和无形的疾病经历。
26岁时,在我为论文收集数据的最后一天,我的风湿病医生在我的抗双链DNA血液测试呈阳性后,自信地诊断我患有SLE具体的红斑狼疮。
在几个月内,我被诊断出患有两种致残的疾病,我被迫面对不确定性、缺乏控制,以及我自己的死亡。我不知道哪一个最难以接受。
感觉就像人生的一个重要篇章结束了。生活与疾病,不是生命作为疾病开始了。
在我的硕士论文面试期间,一位患有SLE的年轻女性与我分享了以下观点:
“一开始,一切都很耗人。从我确诊的那一刻起,甚至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它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生活就是狼疮。(它)影响了我所做的一切……(但)过了一段时间,(它)太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狼疮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身份演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学会带病生活的关键是学会接受生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用另一位参与者的话来说强直性脊柱炎“当你患有慢性疾病时,你几乎每天都要经历悲伤的过程。因为几乎每一天都不一样。”
能够接受疾病是那些能够获得医疗保健、对治疗反应良好、症状减轻的人所享有的特权。这些病人有一个安全网,使他们有可能活下去与生病,知道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会得到医疗和经济上的照顾。
可悲的是,对于许多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不平等造成了这样一种现实,即一些人甚至对自己的疾病都看不见,这不仅是因为缺乏医疗保健,而且是因为缺乏卫生知识。
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体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怎么能识别出什么时候出了问题?
有一个
的美国狼疮基金会报告称,狼疮对黑人和西班牙裔女性的影响几乎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的三倍。这些女性通常患有更严重的疾病,死亡率是白人女性的两到三倍。然而,在红斑狼疮的临床试验中,有色人种女性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对于每一个被诊断出来的人来说,由于缺乏医疗保险或获得医疗服务,会有更多的“勉强度日”症状。
改善狼疮的诊断和治疗时间要求我们的医疗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革。获得负担得起的、合格的医疗保健是一项人权,人们的关切和治疗目标应该得到证实。
每个人都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身体和情感健康需要什么,所以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亲人应该知道问他们而且听.
27岁时,我的风湿病医生告诉我,新的血液测试结果是低积极提示可能涉及心脏、肺和肌肉骨骼狼疮。这种症状还伴随着我脸上的新皮疹。
“这是一个低阳性,所以不是积极的我的风湿病医生挥动着爵士般的手说。“但这并不消极。”
这低积极导致大量的门诊检查:x射线,一个超声心动图,一个肺功能检查和小瓶的血液工作。我的伴侣把我抱在厨房里,我面对着这种新的疾病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说。
所以我们等待。
几周后,广泛的测试结果恢复“正常”,时钟重置。
“我们一年后再检查,”我的风湿病医生说,我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关于慢性疾病,最难以接受的事情之一是,即使治疗可以改善或控制症状,但它永远不会在.
我的狼疮症状仍然很轻微,我和医生们都在努力保持这种状态。虽然从我在大学的症状开始,我已经走了很远,但对于前面的路,我仍然有很多不知道的。
所以我尽我所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过好每一天。
杰奎琳·n·甘宁(Jacqueline N. Gunning)是居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健康传播研究员和作家。她的研究兴趣在于慢性疾病、残疾和性与生殖健康之间的联系,并对确定沟通如何支持个人导航破坏性健康事件感兴趣。她拥有两个传播学学位:爱默生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的文学硕士学位,完成了一篇研究成年期自身免疫疾病的论文。她在亲密交流实验室研究健康信息传递、决策制定和医疗代理,今年秋天将在康涅狄格大学开始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